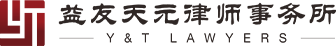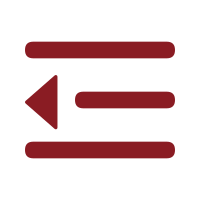益友视点丨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相关法律问题剖析
时间:2025-03-04 作者:益友天元

一、引言 在公司治理中,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犹如一把双刃剑,既可能为公司带来协同效应与发展机遇,也潜藏着利益输送的风险,成为高悬于中小股东和债权人权益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一现象在公司运营管理中极为普遍,已成为公司治理领域重点关注与监管的核心地带。控股股东在股东会决议涉及自身除关联担保外的关联交易事项时,是否应当回避表决,公司法对此并未给出明确的规定,这种“留白”,究竟是立法者基于复杂利益考量与法律技术权衡后有意留下的弹性空间,还是在法律演进过程中尚未填补的空白,值得深入探究。
二、现有法律、司法解释等的规定
《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五条关于关联关系的定义为:“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该定义为准确界定关联交易提供了关键依据。 《公司法》第十五条第二、三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应当经股东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这一规定明确了在涉及自身担保关联交易的股东会决议中,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回避义务。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董事会对本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至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事项决议时,关联董事不得参与表决,其表决权不计入表决权总数。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当将该事项提交股东会审议。”该条明确规定董、监、高自我交易和关联交易、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和同业竞争的,应当主动向公司汇报,并经董事会决议通过,且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如果回避后不能达到法定人数,还需要提交股东会决定。但是,对于此种情况,涉及关联交易的股东是否需要回避,法律就没有再规定。只有在相关上市公司管理规则中对上市公司确有相关监管规则予以明确和细致的要求,关联股东通常需要回避表决,也不得代理其他股东行使表决权,以保障中小股东的知情权和表决权,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三、司法实践
最高法民事审判第二庭在2024年10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理解与适用(下)》第830页中指出,“对自我交易和关联交易、谋取公司商业机会、竞业行为等事项表决时,与实施该行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关联关系的股东是否应当回避,不得行使表决权?对此,本条规定未予明确。”“理论上,关联股东是待决议事项的利益相关方,倾向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行为人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故其参与待决议事项表决时,多数情况下,无法公正地作出最符合公司利益的判断。从这一角度,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更利于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然而,实践中,也不乏关联股东为维护公司利益而理性行使表决权的情况。由此,我们认为,不应 ‘一刀切’地规定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或不回避表决,而应以是否符合公司利益作为衡量标准,由人民法院在具体案件中对关联股东是否回避作出分析和判断。” 在目前能搜集到的案例中,我们发现存在判决标准不统一、二审被改判的情形。在贵州某矿业投资公司与贵州某能化公司、安顺某公司等公司决议及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中,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黔高民商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认为:“本案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内容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应当根据《公司法》《民法通则》等有关效力性、禁止性规范来作出认定。公司对外投资,如果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司法不宜干预。本案中,董事会及股东会决议中的关联交易事项涉及东圣公司部分股东及董事的个人利益,但上述东圣公司股东或者董事明知存在关联关系却不回避,并利用其股东或者董事的权利行使表决权,违反了《公司法》禁止性规定。其决议内容应属无效。”但最高人民法院(2017)作出的最高法民终41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公司决议是否系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以及是否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不能仅因涉及关联交易,就认定股东会、董事会当然无效。参与表决的董事及股东代表与决议事项虽具有关联关系,但法律并未对其行使表决权作出限制。”最终,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 李某亮与北京某建材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京03民终709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本案中, 2019 年4 月 2 日临时股东会决议第一项内容系涉及北京某建材公司与林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确定, 林某作为关联交易方及控股股东,对股东会决议通过与否有决定性影响,故不应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判断关联交易是否损害公司利益的关键为该交易是否公平公允,不仅应审查交易程序、关联交易信息披露是否充分,更应从交易的实质内容即根据对价是否公允、是否符合正常的商业交易原则等方面进行审查。……本案中,如前所述,林某与北京某建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涉案股权转让系关联交易,在林某未对关联交易回避表决的情况下,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损害北京某建材公司等第三人利益之情形,应认定为无效。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综合司法实践可见,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也是有一定规则可循的:首先,原则上认可关联股东表决权,但对其行使施加必要限制;其次,建立“程序+实质”的双重审查标准,如果关联交易明显损害公司利益,且控股股东未回避表决,基于保护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法院可能会认定该股东会决议无效或可撤销;最后,注重个案平衡,基于实践中情况的复杂多样,若关联交易虽存在关联关系,但交易本身具有商业合理性且价格公允,法院在判断时会更加谨慎,并非一概认定未回避的股东会决议无效。这种裁判方法既维护了公司治理秩序,又保障了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我们认为,根据司法实践,相关观点已经酝酿成熟,适合时机对此做出统一规定,更有利于统一裁判尺度和引导当事人合理行使表决权。
四、中小股东及债权人救济途径
非上市公司具有较强的人合性特征,法律更倾向于尊重公司意思自治,允许股东在公司章程中对控股股东在关联交易中的回避表决等问题进行明确约定,尽量减少法律的不必要干预。但法律同时兼顾公平原则,对于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债权人合法利益的行为,也规定了相应的救济途径。
(一) 中小股东救济途径 1、决议撤销、确认无效或不成立之诉:若中小股东认为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的股东会决议存在程序违法、程序或内容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可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法院撤销。如果程序严重缺失成立要件,比如应当召开股东会而没有召开等,还可以依法请求确认不成立。如果决议内容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可请求法院确认无效。 2、损害赔偿之诉:当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进而间接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时,中小股东可以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代表公司对控股股东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从而维护公司和自身权益。 3、请求公司收购股份之诉:《公司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对于公司连续五年盈利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股东会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对这些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要求公司按照合理价格收购其股权。或者控股股东存在滥用股东权利,严重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的,中小股东也有权请求公司收购其股权。
(二) 债权人救济途径 1、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公司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如果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严重损害公司利益,影响公司偿债能力,债权人可以依据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直接要求控股股东或关联公司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代位权诉讼:当公司没有清偿能力,又因为被控股股东控制等原因怠于行使对控股股东因关联交易产生的一般债权,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时,债权人可以根据《民法典》中关于代位权的规定,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公司对控股股东的债权 。 3、债权人撤销权诉讼:当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或者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九条规定,请求法院撤销债务的人的行为。 综上所述,在涉及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的股东会决议中的控股股东回避问题较为复杂,只有涉及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明确规定了回避制度,对于其它关联交易没有明确规定回避义务。但为防范控股股东通过不当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公司法通过相关救济途径的法律规定为中小股东、债权人提供了较多否定其决议全部或部分效力的权利救济措施。无论是中小股东还是债权人,在面对控股股东可能存在的不当关联交易时,都可以充分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刘长伟 高级合伙人 david.liu@yiyou.com.cn 姚 洁 律 师 jane.yao@yiyou.com.cn
免责声明: 以上资料仅供您参考和信息分享,不能被视为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就任何特定事项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结论。在没有获得本所法律或其他专业意见之前,本文内容不应作为您行动或不行动的依据,我们亦不对此承担任何责任。如您有任何具体法律问题或法律委托事务,请您与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联系。